权益颓势难掩,建信基金“独立性”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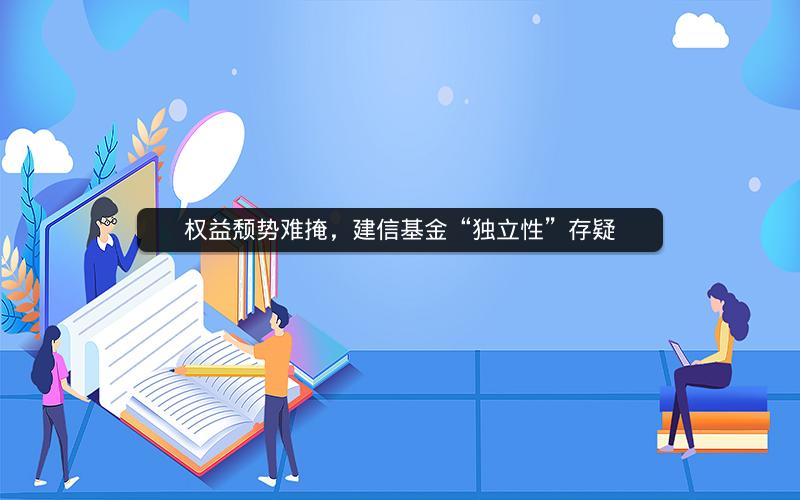
总管理规模正逼近万亿门槛,但最能体现其投研硬实力的非货规模,却陷入了持续缩水的尴尬境地。尽管背靠建设银行这棵“大树”,建信基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然难以证明自身的独立价值。
若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在发行渠道、投资策略乃至产品布局上均深度依赖股东资源,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价值便难免受到质疑。建信基金的现状,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体现。
尽管今年市场环境整体向好,硬科技等板块表现突出,多家同业机构的权益类基金净值实现翻倍增长,建信基金的非货币基金规模却不升反降——从2024年初的2058.32亿元降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1802.02亿元。
受权益类产品业绩不振及降费的影响,建信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也从2022年的23.63亿元下滑至目前的20.94亿元,净利润由11.71亿元收缩至8.44亿元。
尽管背靠建设银行这棵“大树”,在资源获取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建信基金却未能在业绩回报上实现对股东的有效反哺,其高度依赖股东体系的局限性也由此进一步凸显。
权益产品
缺位
近日,公募基金2025年三季报陆续披露。背靠建设银行的建信基金整体规模持续扩张,已逼近万亿元大关。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建信基金总管理规模达到9636.29亿元,较年初增长734.91亿元,在全行业中排名第11位。
然而,规模增长的背后结构并不均衡,主要依赖货币型基金的拉动。具体来看,其货币型基金规模从年初的7000.81亿元上升至7834.26亿元,增长833.45亿元,在全行业排名第2,仅次于以余额宝起家的天弘基金。
与货币基金规模快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信基金的非货币基金规模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其非货规模从2024年初的2058.32亿元降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1802.02亿元,累计减少256.30亿元,行业排名从第24位滑落至第29位。
在非货产品线中,建信基金曾经的优势板块——债券型基金的竞争力正逐步减弱。2018年之前,该公司债基排名一度进入行业前5,而目前规模仅为1281.92亿元,排名已跌至第27位。
权益类基金的持续疲软,则是拖累非货规模的主因。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公司股票型基金规模为233.01亿元,排名第25,较2024年初下降6.86亿元;混合型基金规模为172.46亿元,较年初缩水40.51亿元。
进一步分析可见,尽管权益产品数量近百只,但整体呈现“多而不强”的局面。数据显示,建信基金旗下59只股票型基金中,47只规模不足5亿元,仅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A与建信新能源行业股票A两只产品规模超过30亿元;41只混合型基金中,27只规模低于3亿元。
业绩表现不佳进一步削弱了产品吸引力,形成“业绩差→规模缩”的负向循环。剔除指数产品后,建信基金旗下63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28只近一年收益率跑输沪深300指数,更有11只收益为负,反映出主动管理能力的不足。
部分产品业绩不振,主要源于配置过于集中,未能适应市场风格变化。以建信臻选混合为例,该基金长期重仓白酒与地产板块。据Choice统计,2022年末其房地产持仓占比为17.68%,白酒占比13.26%,合计超过三成。
2023年至2025年间,上述板块持续回调,拖累基金业绩。该基金自2021年成立以来收益率为-11.22%,规模从成立时的51.37亿元降至20.81亿元,近乎腰斩。
规模仅次于该产品的建信兴润一年持有混合,同样因持仓集中、节奏把握不佳,自成立以来收益率仅为-22.42%,规模也从43.52亿元下滑至16.61亿元。
除产品规模偏小之外,建信基金在权益投资领域也缺乏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基金经理。公司目前尚未出现如张坤、刘彦春级别的
“顶流”投资经理,导致市场对其主动管理能力的认知较为模糊。
在投研队伍建设方面,建信基金早期曾培养出陶灿、姜锋等一批骨干,但此后自主培养人才的能力未见显著提升,更多依赖外部引进。例如,周智硕此前任职于工银瑞信,姚锦来自天弘基金,田元泉出身安邦资管,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邵卓则来自广发证券。
据Choice数据统计,建信基金现有65名基金经理中,34人管理经验不足5年。在为数不多的资深基金经理中,能够支撑公司主动权益产品线的或许仅有陶灿一人。三季报显示,他在管的6只基金合计规模为61.51亿元,约占公司主动权益总规模的23.65%。
陶灿是建信基金的元老,2007年7月加入,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职务,现任权益投资部执行总经理。
与此同时,建信基金的权益投研人才也在不断流失。2024年,与陶灿并称公司“权益双将”的姜锋因个人原因离职。离职前,他共管理6只基金,合计规模为22.2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姜锋所管产品中包含2只仍处封闭期的基金。根据相关规定,若在封闭期内主动离职且无特殊原因,其基金经理资格将面临两年内无法注册的限制。
2025年1月,建信基金再次发布公告,周智硕因个人原因离任。他于2020年6月加入公司,最高管理规模一度达到115.56亿元。
离职后,周智硕于次月加入广发基金。截至目前,他已管理6只产品,规模达192.92亿元。相比之下,建信基金全部混合型基金的总规模仅为172.46亿元,不及周智硕一人的在管规模。
管理费
暴跌
权益产品线的缺位,直接拖累了建信基金的管理费收入。
数据显示,2022年建信基金管理费收入达到历史峰值,为23.63亿元,较2021年增长5.73亿元,增幅显著。然而,这一增长未能持续。2023年,公司管理费收入回落至22.44亿元;进入2024年,进一步萎缩至20.94亿元,收入持续承压。
从费率结构来看,权益类产品通常收取
1.0%–1.5%的管理费,远高于货币基金等低费率产品,理应具备更强的盈利贡献能力,但近年来建信基金权益产品规模持续下滑,严重制约了其收入增长潜力。
据Choice数据统计,2022年,建信新能源、建信兴润一年持有、建信臻选、建信优化配置等57只权益基金合计资产净值约为409.87亿元,贡献管理费收入6.65亿元。而到2024年,这批产品资产净值已跌至239亿元,管理费收入也大幅缩水至3.42亿元,跌幅接近50%。
以建信兴润一年持有为例,2022年其资产净值为31.46亿元,管理费收入为5725.71万元;至2024年,资产净值降至16.26亿元,管理费收入也下滑至2058.82万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信基金货币基金在2022年贡献管理费收入11.47亿元,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12.08亿元。权益产品管理费的大幅下滑,与货币基金的稳健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出公司在高费率权益产品布局上的结构性短板。
管理费收入的持续下滑,直接拖累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据控股股东建设银行的年报披露,2022年至2024年,建信基金全年净利润分别为11.71亿元、8.83亿元和8.44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39%、-24.59%和-4.42%,净利润连续两年负增长。
盈利能力的下滑进一步引发高层人事持续动荡。2022年3月,市场传出建行体系中层管理层密集调整的消息,涉及总行、各分行及多家子公司。同年5月,建信基金公告称,原董事长孙志晨与副总裁马勇均因“股东安排”离任。
仅两个月后,56岁的刘军于2022年7月出任董事长,但任职仅8个月后,于2023年2月同样因“股东安排”卸任,由总裁张军红暂代董事长职务。
人事动荡在2023年持续加剧。1月,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吴灵玲离职;3月,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首席信息官张威威离任,由张力铮接任副总裁。同年9月,生柳荣出任董事长,张军红不再代职。
2024年10月,莫红新出任副总裁;12月,张军红卸任总裁,由谢海玉接任。2025年7月,宫永媛卸任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首席信息官职务,刘大超于次月拟任副总裁。
主体性
存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通常而言,头部基金公司普遍采取“股东把握战略方向、专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经营”的治理架构,以实现战略高度与业务专业性之间的有效结合。
然而,建信基金自成立以来,更接近于建设银行体系内部的一个延伸部门。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几乎全部由建行内部委派,管理层普遍缺乏公募基金行业的从业经验,尤其在权益投资等关键领域能力储备不足,这逐渐演变为制约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瓶颈。
具体来看,建信基金的首任董事长江先周曾任建设银行托管部总经理,首任总经理孙志晨则来自建行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此后多届管理层也延续了这一内部输送的传统。
在董事长层面,许会斌曾任建设银行批发业务总监,刘军则来自建行广东省分行;而现任董事长生柳荣,在就任前担任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
总经理方面,孙志晨的接任者张军红,曾任建设银行总行投资托管部副总经理。其后,谢海玉接替张军红出任总裁。
值得关注的是,谢海玉同样出身建行体系,自2001年加入建行后,长期在总行资金部、金融市场部等部门任职。即便后续兼任建信金投相关职务,她仍缺乏公募基金管理所需的一线投资经验。
不仅如此,公司其余四位副总裁——刘大超、莫红、张铮、吴曙明,也均来自建行体系,分别分管财务、营销、信息技术与督察工作。整个管理层中,无一人具备公募基金行业背景。
银行的对公、零售等传统业务逻辑,与公募基金所强调的投资管理、市场研判存在本质差异。尽管在固收领域两者有所重合,但在权益投资、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银行系经验难以直接转化。
因此,建信基金“外行领导内行”的治理结构,直接制约了其核心业务的专业化进程。无论是在投研体系的建设,还是在市场化营销与品牌塑造方面,公司均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公募行业竞争中实现实质性突破。
相比之下,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等表现更为出色的银行系基金公司,其高管团队的专业性更强。例如,交银施罗德的三任总经理莫泰山、战龙、谢卫均为市场化选聘,且均具备证券、基金领域的相关从业经历。
此外,建行体系内的子公司布局非常完整——建行自身投资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毫无障碍,旗下理财子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均可参与债市及货币市场投资。
在此背景下,若建信基金也仅重复参与同类业务,其在资产管理中的主动性、主体性以及差异化定位将难以体现,甚至可能逐渐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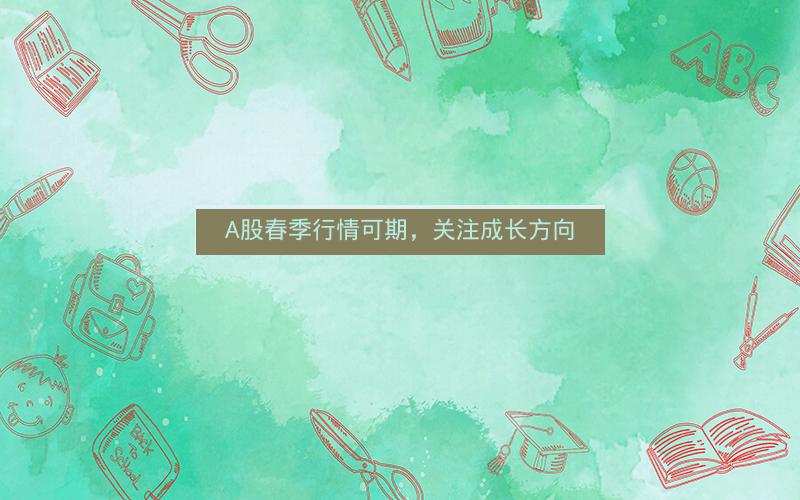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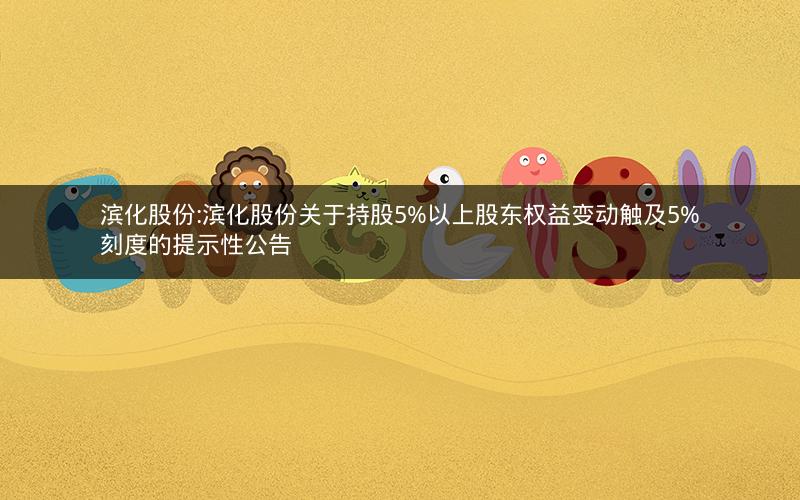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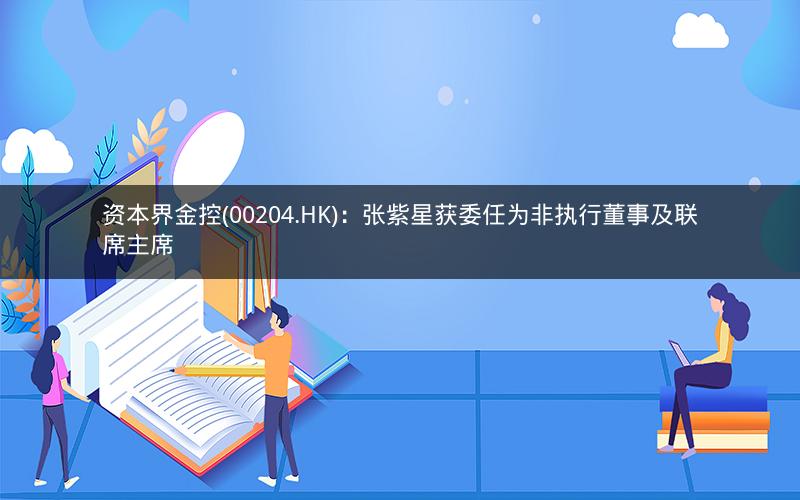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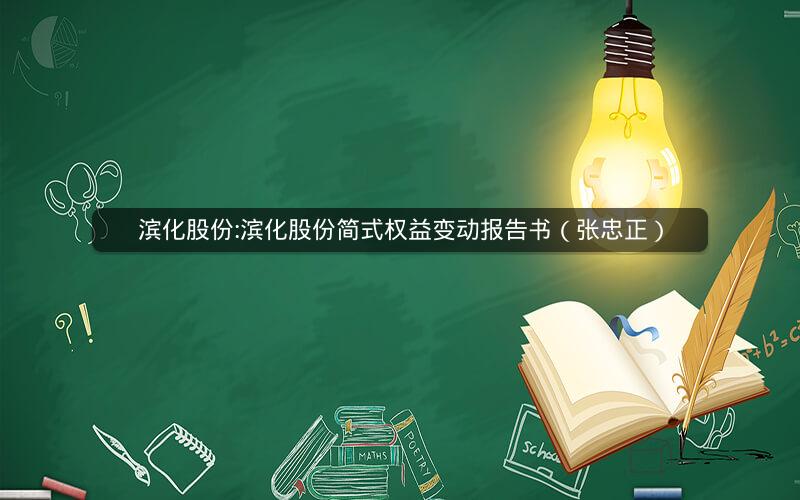
评论留言
暂时没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