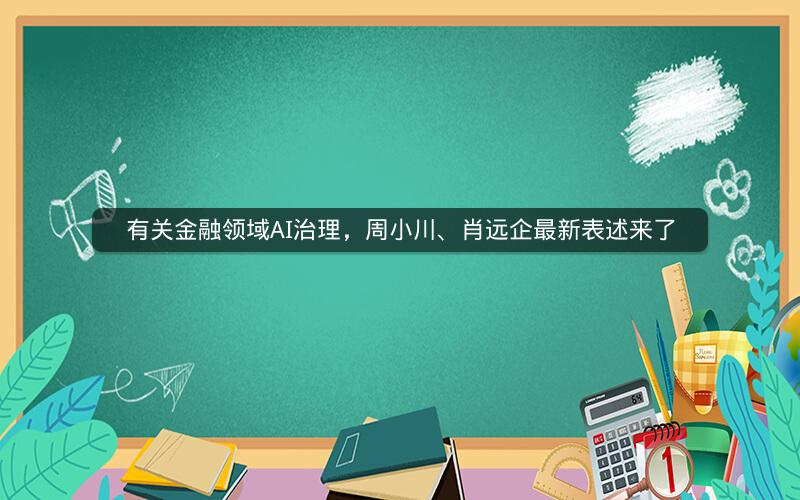
文/高歌、李悦
10月23日,在2025年外滩年会的首场圆桌讨论中,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结合既往经验与现有观察给出了最新的观点。
在今年的外滩年会上科技话题前置,“金融领域的AI治理与国际合作”成为首场圆桌议题。
外滩年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2023)、欧洲央行原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用“3-4-5”来梳理此次年会议程的关键线索。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绿色转型与气候转型、全球变化和国际秩序变革、AI与新兴技术的会议场次,足见AI这一关键议题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不止一位与会者提到了“索罗悖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提出,人们对大型计算机投入巨资,却没有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或许AI转化为生产率跃升也需要更多时间,但AI所带来的冲击与改变也是前所未有的,“索罗悖论”或许并不会重演,因为在这一领域,我们正在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AI究竟是一种边际性的技术工具进步,还是更像蒸汽机、电力,是全方位重塑行业业态的根本性变革?
面对这一问题,周小川的基本判断是:从金融的角度来看,AI是在历史上信息处理、IT和自动化基础上的又一次新的边际变化――但这个边际变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涉及银行主要业务、客户行为与监管等诸多层面。
更高维度上,AI对于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双支柱”政策框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未来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许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
“央行关心的经济金融不稳定问题,往往有一个积累过程,然后可能突然到“明斯基时刻”爆发。这个过程与我们过去所说的正弦波式周期变动不太一样。严格地说,各国央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度我认为还不够。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可能有泡沫,但我们并不清楚它会在何时破裂。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长期数据、多次事件中学习,大致预知什么样的泡沫积累,在什么时点、什么触发环境下爆发的概率是多大。”周小川表示,“过去金融系统依赖的是大量的结构性数据,不太需要情感数据或长文本。风险、定价、营销等都是在结构性数据基础上得到的。但分析历史事件、泡沫积累、明斯基时刻的出现、事后处理及对错评估,这些需要更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处理非结构性数据、多模态信息,甚至考虑社会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传染、蔓延。因此人工智能也开辟了很多新领域,但距离真正应用还有相当距离。”
肖远企认为,AI的应用究竟是边际性改变、增量性变革,还是根本性颠覆,这还需要继续观察,但至少在目前,AI应用所带来的风险,与历史上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在金融领域应用时产生的风险类似,目前或许难以定论。
但从历史视角看,肖远企认为,过去几轮科技革命在金融领域主要带来的是增量风险和边际风险――风险的成因、路径和形态有所变化,但金融行业面临的根本性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并未发生革命性改变。
01 “慢变量需要慢处理”
在AI影响来袭之前,银行业已深度具备IT基因。
周小川回溯历史指出,银行业的性质在过去六七十年间已发生根本转变。“银行业正在从传统银行转变为数据处理行业,”他援引25年前与研究生合著的文章观点称,如今银行的支付、定价、风险计量及市场营销等核心业务,均已高度依赖数据分析和模型计算。
在此进程中,人机关系经历了深刻演变。“从过去人主导、机器辅助,演变为人主要作为机器与客户之间的界面。”周小川表示,这一历史性转变已经持续了六七十年,且为AI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系统积累的海量数据(603138),使得机器学习能够推动传统模型向智能推理模型升级。
不过,尽管AI浪潮中生成式与多模态技术备受关注,但周小川强调,银行业因其特性,主要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推理模型。“基于这一特点,银行未来结构会进一步向这个方向发展,”他明确表示,“银行的从业人员规模会显著受到影响和减少。”
这一判断还基于客户行为的深刻变迁。周小川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客户更习惯与机器互动,“不太愿意或认为没有必要人工介入”。这种双向变化正推动AI在银行业的支付、定价、风险管理和市场推广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在监管领域,AI同样带来机遇与挑战。周小川以反洗钱为例,指出当前系统可以利用机器学习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洗钱等线索,已取得很大进展。在金融稳定领域,他认为,机器学习有望从历史金融数据中推理预知“明斯基时刻”的爆发概率,但需要处理非结构性数据、多模态信息乃至考虑社会情绪。
他指出,人工智能也开辟了很多新领域,但距离真正应用还有相当距离。
但他也提示,AI模型的“黑箱”特性与监管要求的透明度存在矛盾。同时,若AI模型过度依赖短期高频数据,其产出可能与金融稳健所需的长期性、基础面导向产生偏差。“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
针对AI对央行“双支柱”政策框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影响问题,周小川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
他指出,一方面,AI可以在物价和微观行为的数据收集、处理、模式识别和推理方面影响货币政策决定。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是“慢变量”,它随经济周期或经济变化而调整,而这个变化不会太快。“货币政策不可能对每天的蔬菜价格变化做出响应,”他指出,过快响应反而可能引发不必要波动。因此,慢变量需要慢处理。
02 边际性改变还是根本性颠覆,仍需观察
AI帮助金融机构对内提升运营效率,对外更好地提供服务和产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员工数量庞大,随着AI效率提升,是否会带来内部员工安置的压力?
对此,肖远企回应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金融机构单纯因AI应用而出现员工安置压力的案例。我们认为,员工是金融机构最有效的生产力,每一位员工都在创造价值。尽管AI发展迅猛,应用广泛,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目前AI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其作用仍是辅助性的,无法取代人的决策。”
他以柜员服务举例称,AI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柜员与客户之间个性化的互动。在信贷、保险定价、定损、精算等关键领域,仍然离不开人的专业判断。“在金融领域,人才始终是我们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资产。”
事实上,AI的应用还可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但AI的应用究竟是边际性改变、增量性变革,还是根本性颠覆,肖远企认为仍需继续观察。
同样需要密切关注的还有AI应用带来的风险。“与历史上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在金融领域应用时产生的风险类似,目前或许难以定论,但从历史视角看,过去几轮科技革命在金融领域主要带来的是增量风险和边际风险――风险的成因、路径和形态有所变化,但金融行业面临的根本性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并未发生革命性改变。”
具体到这一轮AI变革对金融领域带来的风险,肖远企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观察。
从微观来说,对单家金融机构而言,主要有两类新型或增量风险:一是模型稳定性风险。这一轮AI应用高度依赖模型支撑业务拓展,因此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变得至关重要。二是数据治理风险。这涉及数据来源的选择、数据质量的把控以及事后的评估与监测程序,也就是数据治理的程序。这两类风险对单个机构非常关键。
对整个行业而言,则主要有两类增量风险:一是集中度风险。金融行业在AI模型技术上可能会依赖少数技术开发能力强、稳定性高、资源投入大的服务提供商。同时,大型金融机构在资源投入上可能比小型机构更具优势,可能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这一点有待观察。二是决策趋同风险。由于所使用的模型和数据相对标准化和集中,金融机构在决策依据上可能趋同,进而导致行业整体决策同质化。如果趋同性过高,可能引发“共振”效应,这是需要关注的。
“当然,一个良好、稳定、有效的金融结构需要多元化的参与者与市场平台。因此,我们也必须关注AI对整个金融结构变化的潜在影响。”肖远企表示。
从当前实际应用情况看,目前,AI在金融行业主要用于优化业务流程和对外服务。从金融监管总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首先是中后台运营的智能化。这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已应用得比较广泛,覆盖了数据收集、加工、信息甄别与识别,以及客户评估等多个环节。其次是在客户交流方面。许多金融机构在客户关系管理,包括营销、维护和问题解答等方面,都普遍应用了AI技术。第三是在金融产品提供方面。AI的应用带来了双重效益:对内,它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外,则使它们能够为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更个性化、更精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更有效地解答问题和满足需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