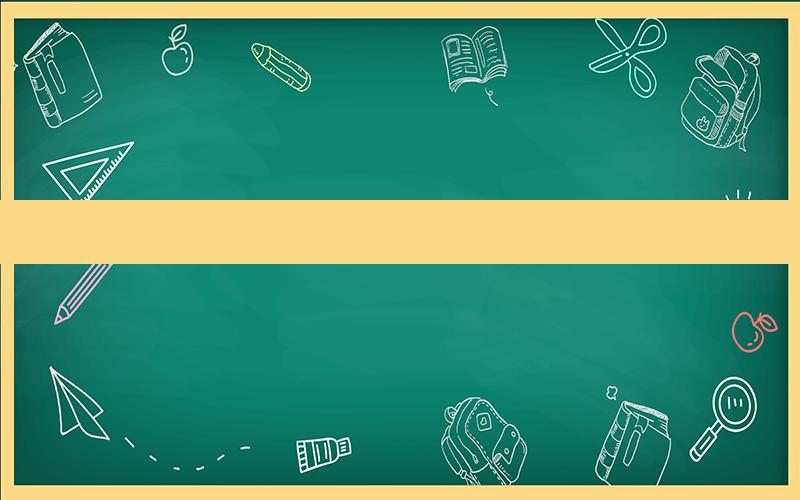
28亿元!高瓴再度出手,拿下医药巨头资产。
10月26日,药明康德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药明拟以28亿元的基准股权转让价款转让医疗资产,受让方均系高瓴投资(以下简称“高瓴”)通过旗下私募股权基金为本次交易目的新设立的公司。
上述资产出售公告发布同日,药明康德还发布了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28.57亿元,同比增长18.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76亿元,同比增长84.84%。
药明康德一边交出净利润同比大涨84.84%的亮眼三季报,一边却以28亿元将临床研究业务出售给高瓴,这一“增”一“减”的鲜明对比,令市场不禁追问:为何在业绩大好时选择“瘦身”?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药明康德继去年剥离美国细胞基因治疗业务单元(WuXi ATU)等资产后,又一次“瘦身”之举。无独有偶,百时美施贵宝(BMS)此前也已将其在华合资公司股份售予高瓴。业内观察指出,面对创新药研发的高成本与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大型药企正主动收缩战线,重新审视其业务边界,将资源集中于最核心的领域。
再度“瘦身”的背后
公告显示,津石医药及康德弘翼主要经营临床研究服务业务。2024年药明康德整体临床CRO及SMO业务收入18.1亿元,占总营收比重不足5%。
业绩方面,2024年及2025年前三季度,康德弘翼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91亿、1.86亿,净利润分别为-4247.29万元、-7545.30万元;津石医药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3.38亿元、9.7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13亿元、1.62亿元。
津石医药主要财务信息
对于本次交易,药明康德明确表示,此次剥离是为聚焦药物发现、实验室测试及工艺开发等核心CRDMO领域,交易所得资金将用于加速全球化产能投放,与此前出售WuXiATU英美业务、优化业务结构的逻辑一脉相承。
业内观察指出,此次被剥离的两家子公司分别对应临床CRO与SMO业务。其中,康德弘翼主营I至Ⅳ期临床试验的监查与管理,津石医药则是国内领先的SMO服务机构,拥有规模庞大的临床协调员团队。
而药明康德的优势在于“一体化、端到端”的CRDMO模式,覆盖从药物发现、工艺开发到生产的全过程。对于药明康德而言,出售临床业务给高瓴,一方面可以获得资金,加速全球化和核心产能建设,另一方面可以使管理层更加专注于具有竞争优势的CRDMO业务。
药明康德此次出售临床研究业务,也反映了整个CXO(医药外包)行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过去,行业的增长更多依赖于制药企业将研发生产活动整体外包的渗透率提升。而现在,增长的核心动力转变为对多肽、ADC、寡核苷酸等特定前沿技术领域外包需求的集中爆发。这些新分子类型研发工艺复杂,制药公司更愿意交给具备专门技术和产能的CDMO巨头。
对于药明康德而言,临床CRO业务收入占比不足5%,且其中部分子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继续投入,其回报率远不如将资源押注于与GLP-1等明星药物密切相关的TIDES(寡核苷酸与多肽)业务,是一次顺应技术浪潮的战略聚焦。
高瓴为何接连接手?
药明康德的“减法”并非孤例。今年9月,业内消息显示,BMS宣布已签署协议,将其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的60%股权及数款仅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产品出售给高瓴关联公司。
从跨国巨头BMS到本土龙头药明康德,高瓴接连将两家顶级药企剥离的核心资产收入囊中,这不禁引人深思:为何巨头们在此时不约而同地“做减法”?高瓴又为何逆势而为,频频出手?
公开资料显示,高瓴成立于2005年,专注于医疗健康、制造业、绿色能源、硬科技和消费科技等领域,投资横跨早期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并购投资等阶段,投资人主要来自全球机构投资人。
高瓴在医疗健康领域有着广泛的投资布局。其中,2017年11月,高瓴抓住跨国药企辉瑞战略退出的窗口期,通过旗下控股子公司以约2.86亿美元的现金对价,收购了辉瑞持有的海正辉瑞(后更名为瀚晖制药)49%的股权。
彼时的瀚晖制药,已成为海正药业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现金奶牛”,但海正自身因负债高企、资金紧张,无力以纯现金方式回购股权。到了2020年海正药业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支付”的组合方案,收购高瓴旗下持有的瀚晖制药剩余49%股权,交易对价定为44亿元。
交易完成后,高瓴不再直接持有瀚晖制药股权,而是通过获得海正药业的股权与可转债,一跃成为持股超5%的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战略投资人,并成功锁定董事会席位。
这场持续近三年的投资,最终以高瓴从“子公司股东”到“母公司股东”的身份升级告终。其背后不仅是资本结构的精巧设计,更体现了高瓴在医药领域中善于在传统企业中进行价值挖掘,并通过与企业深度绑定,从而获取回报的独特逻辑。
对于高瓴而言,药明康德此次28亿元出售临床研究业务的交易则是其在医疗健康领域布局的又一落子,凭借其深厚的资本和产业资源,有望挖掘这些临床业务的潜在价值。
编辑:张洁莹
版式编辑:余远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