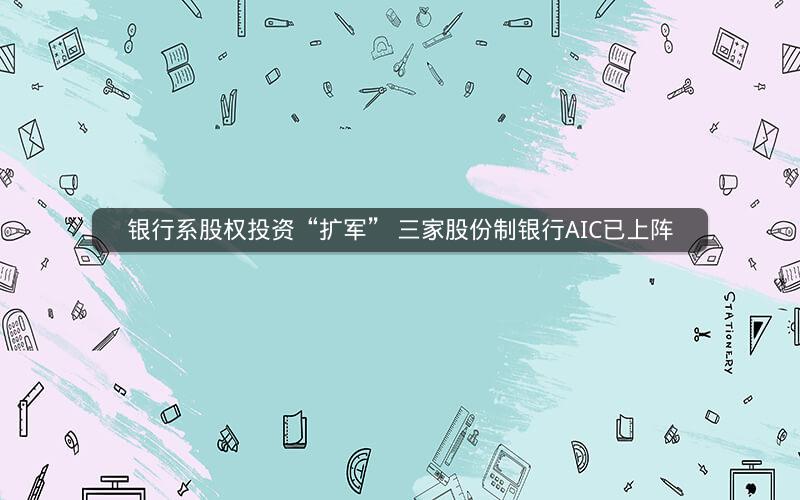
银行系股权投资“扩军”
三家股份制银行AIC已上阵
□ 今年以来,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3家股份制银行以及邮储银行旗下的AIC相继获批筹建,注册资本分别为10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和100亿元。其中,兴银投资、招银投资和信银金投已获批开业
□ AIC试点加速扩围,也折射出银行业希望借助这一工具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开拓业务新空间
继兴银投资获批开业后,近日,再有两家股份制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AIC)获批开业。
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日前分别公告表示,招商银行旗下招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简称“招银投资”)以及中信银行旗下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信银金投”)已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开业。
今年以来,股份制银行在股权投资领域积极布局,AIC从大行试点走向扩围试点,成为银行突破传统信贷模式、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市场各方也对此寄予厚望。
股份行接连入场AIC,也并非偶然。在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信贷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监管部门主动扩大AIC试点范围,释放明确信号,引导商业银行跳出“放贷”到“收息”的单一路径,通过股权直投深度嵌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链条。
三家股份制银行AIC上阵
今年以来,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3家股份制银行以及邮储银行旗下的AIC相继获批筹建,注册资本分别为100亿元、100亿元、150亿元和100亿元。其中,兴银投资、招银投资和信银金投已获批开业,注册地分别设在福州、深圳和广州。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继国有大行之后,股份制银行陆续开始尝试这一新的业务形态,有助于充分发挥其机制灵活、市场敏锐等优势,预计后续将有更多AIC获批筹建。”
作为首家获批筹建的股份制银行AIC,兴银投资打破了自2017年首批5家国有大行设立AIC后长达8年无新增AIC的局面。目前最新进展是——兴银投资近日已在福州正式揭牌,并与4家投资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12家企业签署项目合作协议,意向金额超100亿元。
招银投资则是初始成立时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AIC。在人员安排方面,上证报记者了解到,招银投资的核心管理团队已初步组建。据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董事长由招行副行长雷财华担任,总经理为招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郑新盈;董事包括李翀、齐向昱和李俐,均为招行相关部门负责人。
借力AIC开拓新业务
AIC试点加速扩围,也折射出银行业希望借助这一工具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开拓业务新空间。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员王运金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涉及万亿元规模的监管政策调整,其意义远不止于缓解银行息差压力,核心在于打破传统信贷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引导更多资金精准注入实体经济。
上证报记者从招行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招银投资未来可充分发挥招行在资管领域的多牌照协同效应,提供“资金+资本”一体化的投商行综合服务,并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发挥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优势。
中信银行表示,信银金投的设立是该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关键举措,也是打造综合金融服务的重要一环。其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及股权投资业务。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投资持续升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额已超过3.6万亿元,同比增长8.3%,科技创新及产业转化进程明显加快。然而,科创企业仍普遍处于“缺资金”状态,股权投资市场“融资难”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王运金表示,传统信贷模式高度依赖抵质押物,而科技创新企业往往轻资产、高成长,缺乏充足抵押品,难以通过银行信贷或直接融资获得足够支持。AIC通过股权投资形式,为银行资金合规进入科创领域开辟了新路径,实现了从“不能投”到“可以投”的机制性突破。
从更深层次看,AIC也将推动银行业务模式发生转变。分析人士认为,银行可以借此拓展综合金融服务链条,创新发展多元金融产品,降低对传统信贷业务的利润依赖。这种转型不仅关乎短期收益改善,更是银行主动布局未来优质资产、培育跨周期经营能力的战略突破口。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AIC牌照也展现出独特价值。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张思远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IC设立的初衷就是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帮助企业降杠杆。通过将债权转为股权,不仅能化解不良资产,还能以股权投资对冲传统信贷风险,正成为银行盘活存量信贷资源、构建多维风险防御体系的有效工具。”
仍面临结构性挑战
银行系AIC的扩容将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业内专家认为,AIC凭借其“银行系”特有的品牌信誉和资源整合能力,与传统的VC/PE机构及政府引导基金形成有效互补。
王运金进一步表示,AIC虽资金体量庞大,但其投资行为受到内部运营框架与外部监管指标的双重约束。例如,股权投资基金对单一项目的投资占比存在上限,这为市场化投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合作空间。在他看来,AIC资金、财政资金、保险资金、社会资本等各类“耐心资本”将共同构成硬科技投资生态的重要参与方。
然而,AIC的发展仍面临结构性挑战。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上证报记者,最核心的矛盾在于银行固有的稳健经营理念与股权投资高风险属性之间的冲突。建立符合股权投资规律的尽职免责机制和激励约束体系,提升对早期项目的风险容忍度,成为AIC实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此外,专业人才储备、决策效率提升和退出路径规划也都是亟待突破的瓶颈。
针对这些挑战,王运金建议:一方面需要建立与股权投资特性匹配的跨周期考核体系和市场化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完善尽职免责制度细则,在符合专业合规要求的前提下明确风险容忍边界。
除了机制创新,资本约束的松绑同样有现实需求。王运金称,逐步降低投资风险权重至关重要。当前AIC股权投资风险权重按1250%计算,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也造成了显著压力,
因此,张思远认为,下一步政策创新的关键突破口在于优化资本监管与退出机制,对AIC股权投资实施风险权重的差异化调整,将成为释放其万亿级潜力的核心钥匙。他建议:加快试点AIC股权挂牌转让平台、发展S基金市场,破解“投得进、退不出”难题;同时推动AIC与险资、产业资本协同设立基金,配套税收优惠,吸引多元长期资本,系统激活其“耐心资本”功能。















发布评论